再看《闯关东》才懂:一郎娶了守活寡18年的秀儿还割腕自尽的隐情
2025-02-14 11:41:04
影评人到底是干什么吃的?
文|三九
作者简介:爱看电影,日常搬砖,梅雪风老师的小粉丝。

赛人:影评人、媒体人,著有《与光同尘》。
梅雪风:影评人、媒体人,著有《虚无的质感》。
1
看完《村戏》,影评人梅雪风问导演郑大圣,为什么总是用一些微小的,跳脱出时代的人去呈现宏大?
郑导有些意外,他琢磨了一会儿说,感谢你帮我挖掘到无意识的想法。他说自己会不自觉地关心时代里被甩出去的人,他们没有像大部队一样随波逐流,而是跌落在了缝隙里。
我作为枪稿责任编辑,有幸参与今年的厦门HiShorts!短片节。到场的所有人都是幸运的,在话语、信息满天飞的世界里,大家仍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,并且能被人看到,听到和思索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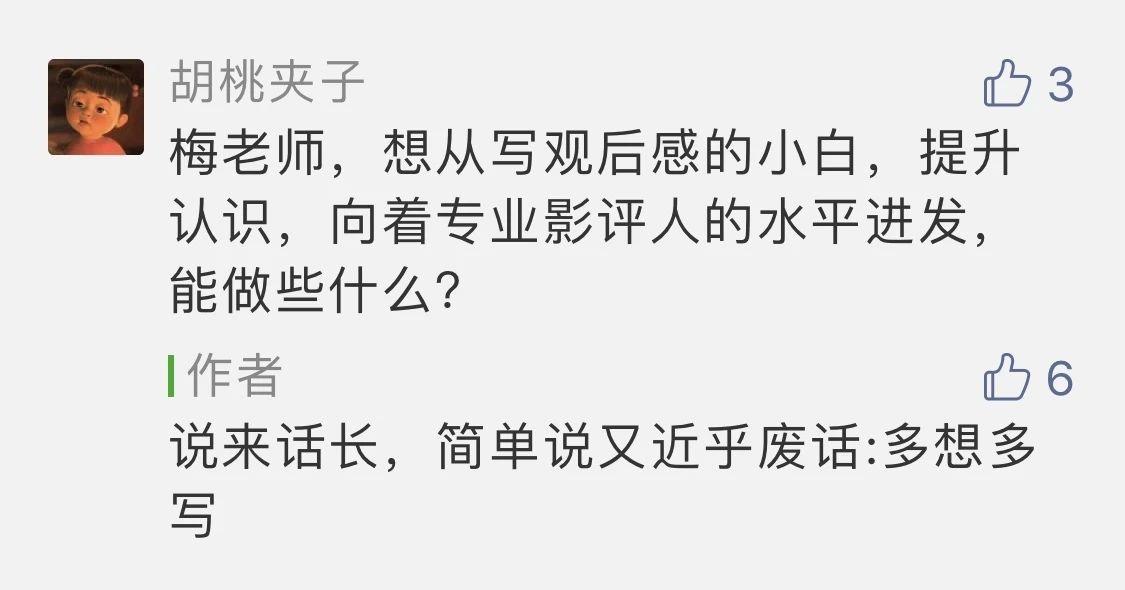
梅老师对于如何写影评的解答(手动狗头)
“影评人是什么”是短片节影评人论坛的主题。作家于一爽说,他们是写影评的人。媒体人娜斯认为,他们提供观影指南。在梅老师看来,影评人在用自己的思想和观点,把观众引向创作者的内心。
是的,影评人是什么?
在人人都能随手写评论的当下,专业的影评人已经“死”了吗?在水军遍地的社交平台上,还有发表真知灼见的影评人吗?
去年开始,我入职枪稿,结识了仰慕已久的雪风老师和赛人老师,这两位湖北老乡,一个理性,一个感性,一个沉默,一个健谈,一个羞涩,一个张扬,一个喜欢窝在家里逗猫,一个爱和朋友把酒言欢。
他们写得出最好的影评,是可爱的人。
当然,更是最能代表“影评人”这个身份和价值的两个杰出样本。可能,要理解“影评人是什么”,在他俩那里,就能见微知著,看一斑而窥全豹。

短片节复审评委
2
“写影评,一定要写出心底最真实的想法。”
梅老师说过最多遍的写作窍门,就是“要做真实的自己”,中年男子教导体,带着浓浓的鸡汤味,老土。问题是,怎样才能做真实的自己?
“我内心的声音总是很矫情。”我说。
“矫情就矫情呗,有什么不好?你看王家卫多矫情,矫情也可以很动人。”
他的文章不矫情。他克制地写出每一句话,力求对人类灵魂的各种游移路径做出最审慎概括。最朴素的文字背后,是他幽微的内省与对外界的深入洞察,还有他严格的控制感。
他本人也时常是“不动声色”的。他认真听对方讲话,记得住许多细节,直视对方的眼睛,不动声色。他有个“to do list”,每天勾掉完成了的任务。至今为止,他已经打卡182次瑜伽肩背僵紧释放,160次跑后拉伸。他已经跑完1000多公里了。
我想,他心里总有股执着的劲儿,从最小处来看,他执着地用一种古早的说法讲“看电影”——“看碟”。他一开始不知道emoji表情里的微笑并不代表微笑,他不明白很多新词的意思,但又觉得在日新月异的数码产品网页里遨游,可比干正经事儿有趣多了。
他像是站在时间之外的人,他看着人和事从他身边流过,并不感觉心潮澎湃。最近几个月,他拿着一部像Kindle一样的黑白墨水屏手机,以便阅读,不问世事,“而且护眼”。

(《监狱风云》剧照)
在厦门的某天清晨,我和梅老师一块儿沿着海边跑步。被前夜的雨水洗过的蓝天,清洁得可以发出声音。他正跑着,突然停下来,拿出iPhone拍照:“我那个黑白手机上没有Keep App,没法打卡装X。”
他总是很诚实,诚实到会打破我们对世界的幻想,会让我在感觉慰藉的同时,又有种失去感。就像他这样写周星驰的《美人鱼》:
“为什么当美人鱼被追捕落在地面上时,你看到的是一种极其写实的画面……有着自然主义的血腥与黏稠?周星驰在这儿就有了一种极其愤世嫉俗的做派,他不是意思一下,他就是要让你如飞机失事般猛然坠落,从幻想中回归人间,让苦痛如巨剑刺穿你的心防。”
又或许他的淡漠感也由诚实中来,他可以懂每个人,但不会刻意追求人和人间的联结。他为读者解惑,又自称“惑者”,他说:“其实我也不明白。理性只是非理性的幌子,让自己自圆其说的技术,驯化不了非理性。大抵如此吧。”他说,“当然,我也是猜的。”但他总猜得到我们说不出的心思。尽管他的文章,不煽情,不谄媚,也不要求共鸣,他庖丁解牛,衣不见血,然后,放下刀,他走了。

(《雨月物语》剧照)
他有次问我:“你是希望年轻一些,还是更喜欢现在?”
“现在吧,”我说,“现在能经历的事情更多。”我词不达意,又无法更精确。
“看来你更喜欢丰富。”他说。
对了,他又说出来了,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个词。他的读者留言里最常见的一句话就是:梅老师说出了我不知该如何表达的感受。
我不知道他是否会偶尔怀念深夜的录像厅和寒冷的哈尔滨,也许从叛逆的青少年时代开始,他已懵懵懂懂意识到,电影给“普通民众的真实的人生制造更多扎实的慰藉,以及生出更靠谱的希望。”后来,他带越来越多的读者走近创作者,让他们看到“每一滴眼泪里,都有整个时代的悲喜,而每一声轻笑里,则都有整个人类的希望”,而他自己会刻意回避仿佛是与导演们更亲近的时刻,他觉得站在那里,看到这么多,恰是刚刚好了。
“‘每年的春天一来 ,实际上也不意味着什么, 但我总觉得要有什么大事发生似的,我的心里总是蠢蠢微动,可等春天整个都过去了,根本什么也没发生......我就很失望,好像错过了什么似的 。’《立春》的台词太动人了,想到这些我都想哭了,虽然哭不出来,”他说,接着看了一眼他的黑白手机:“你看,用了一天了,还有70%的电,是不是很厉害?”

(《风中有多雨做的云》剧照)
3
在论坛边上,我看到了一对小情侣。男孩正兴冲冲地说着话,女孩一动不动地望向他。突然,没有任何预兆的,她一下子抱住了男孩,“哈哈”笑了两声,又松开了。
我瞬间想起了赛人老师说过的一句话:许多拍爱情片的导演,一看就没谈过恋爱。
两个词形容赛人老师:性情中人,文如其人。
在他的各种长评短评里,你总能感受到他丰沛的情感。赛人的文字是极其感性的,他的感性并非情绪化,也不是顾影自怜。他用电影反躬自照,但照出来的绝对不是私人的共鸣,而是一个站在人群中的自我。
他很生动,像一位诗人,指给你电影中明亮的星和幽暗的火;他很温柔,拭去你眼角润出的一滴泪;他又很犀利,犀利到近乎残忍,对电影,对自己,也对你,他每一发直中命门的拷问里都在说,看吧,这是我,这也是你。

(《小丑》剧照)
赛老极爱电影,他说的十句话里有九句都与电影有关。他对当下院线电影的评分近乎苛刻。大家伙都觉得挺好的电影,在他这里只能拿三分。用他自己的话说,如果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》是10分的话。现在的电影有几个能比?《少年的你》能比吗,我给他8分,他配吗?
他说,这样打分,代表着他对中国电影未来的希望,如果所有的电影都是八分九分,那以后更好的电影得拿几分呢?
他在微博里说:
“什么是好的影评,一言难尽。什么是不好的影评,我倒略知一二。那就是穷尽所有的才智,将电影临摹一遍,是故事,也是情感,更有最浮面的形而上,将共鸣凌驾于个性化的表达之上,述说的是绝大观众,不用体悟也能掌握的理解,不用揣摩也能获得的感知。是对真相的漠视,是对思考的拒绝,是对众口一词的拥抱,是对集体意识的屈从。更是对陌生化的抵触,是对视听所营造的’新世界’的仇视。他们永远也不会承认,审美是一种引领,是与我们的此生此世,终将平行的另一端宇宙。”
赛老在他的影评集《与光同尘》里,把他认为的好电影分为四等,普通好的,有气质;更好一点儿的,有性格;再好一些的,富有生命的气息;而最好的,则呈现人类的命运。他说如果让他选一个唯一最喜欢的导演,那就是日本导演成濑巳喜男。成濑的所有作品里,他最爱《浮云》。

(《情迷意乱》剧照)
“你知道《浮云》最后一个镜头是什么吗?”赛老问我。
他总喜欢提问,问我记不记得哪句台词,哪个动作,哪个表情。他似乎记得起所有他看过的电影里的全部细节,这让总是过眼即忘的我深感惭愧。
“最后一个镜头是……男主角在女主角的旁边?”我硬着头皮回答。
“一看你就没看懂这个电影,”赛老说,“他在她旁边跪下。在他终于自知再也无法摆脱这个女人,决定接受命运,接受她时,他死了。这就是他的命运,他是向命运下跪。《情迷意乱》也一样,在嫂子最后犹豫要不要接受小叔子的爱时,小叔子突然意外身亡,这就是命运,命运连犹豫的机会都不给你。”
我什么都说不出来,只能作捂胸口状,长叹一声:“啊!”

(《理查德·朱维尔的哀歌》剧照)
他小时候在家乡小城的电影院里看了来自各个国家的电影,有带字幕的,有配音的。
“你能想象吗,”他说,“我那时候和各行各业的人一块儿坐在电影院里看法国的新浪潮,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,卖菜的大婶、修车的大叔看完费里尼,都在偷偷擦泪。说普通观众看不懂大师艺术的,都是扯淡。”
赛老说,《我和我的祖国》多残忍啊,这盛世,没有一个个体的愿望实现了,连小朋友都无法和心爱的女孩好好告别。
他总能看得到幽微角落。他喜欢电影里带着灵气的表达。他爱说“妙啊”。
“妙啊”是什么?或许是两个在路边晃荡的青年,下意识踢走的那只易拉罐。

(《两个人的车站》剧照,图为女主角柳德米拉·古尔琴柯)
4
影评人是干什么的?他们是引领读者沿着影像的脉络,抵达某种美学、或者真相、或者未知的向导。
梅叔觉得“电影从不比生活更重要”。他喜爱工程师导演杨德昌说:“电影发明以后,人类的生命,比起以前延长了至少三倍。”如果说杨导用影像丰富了人类的生命体验,梅老师作为影评人里的工程师,便是用文字搭建起认知的大厦,试图从艺术里找到世界的规则或真理。或许最终的结论是,世界运行的规则就是没有规则,而所谓真相,也不过是限于某些名词的纷争,但我们跟着他,走过月色下的街道,登上摘星星的高楼,成为更诚实,更善良的人。
而于赛人,电影便是生活本身,那是诗人的酒,是画家的窗,是从四面八方吹来的风,是爱情。我们被电影冲刷得心旌摇曳,一转身,便被他的文字拥抱,被他带去比电影里的远方更远的地方,去看地球彼端的人,如何挨过和我们自身经历类似的小打小闹或者爱恨情仇。世界不就是这样么,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,但人类的悲欢也就那么回事,多往外看看,还有广阔的天地和浩渺的宇宙。
那么,游侠赛人啊,不如我们开怀畅饮,当歌对酒,而禅师雪风呢,不如我们遥望深夜,然后相顾无言。

赛人老师的《与光同尘》封面便是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》的这张剧照。他和梅雪风都很喜欢这部电影。
编辑|浪浪
排版|透纳
THE END
【枪稿系今日头条签约作者】
© 版权所有 未经许可 禁止转载
2025-02-14 11:41:04
2025-02-14 11:38:48
2025-02-14 11:36:32
2025-02-14 11:34:16
2025-02-14 11:32:00
2025-02-13 19:06:43
2025-02-13 19:04:27
2025-02-13 19:02:11
2025-02-13 18:59:55
2025-02-13 18:57:39
2025-02-13 18:55:23
2025-02-13 18:53:07
2025-02-13 18:50:51
2025-02-13 18:48:35
2025-02-13 18:46:19
2025-02-13 04:04:06
2025-02-13 04:01:50
2025-02-13 03:59:34
2025-02-13 03:57:18
2025-02-13 03:55:02